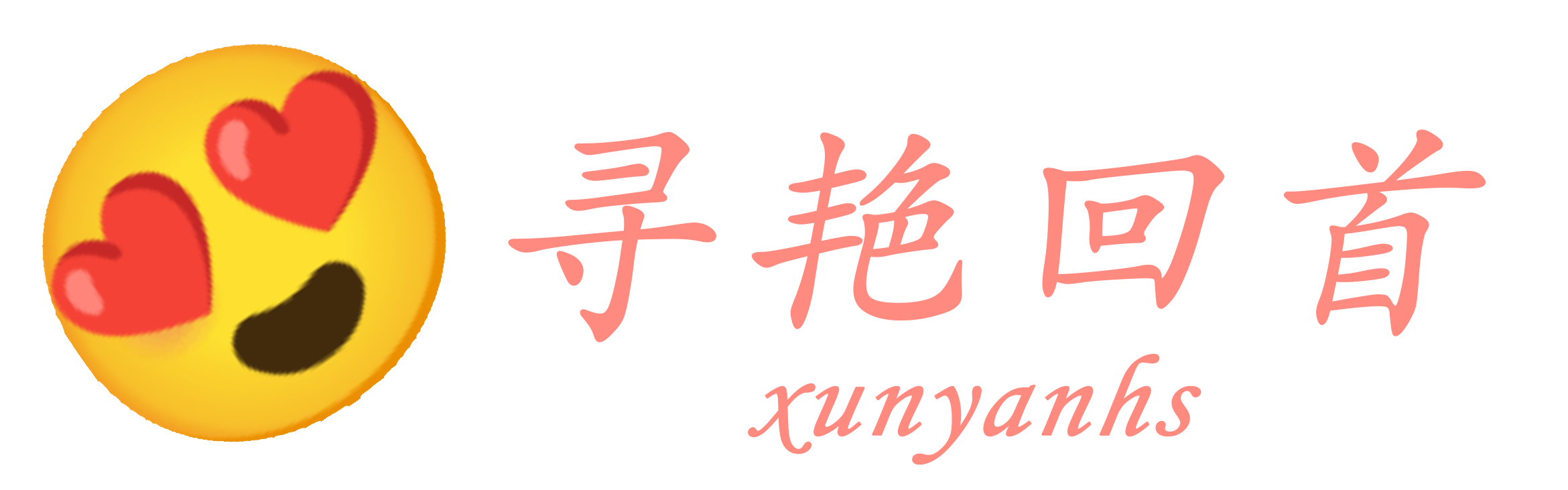视频
网红黑料瓜
巨乳姨妈
人妻熟女
强奸乱伦
欧美精品
萝莉少女
口交颜射
日本精品
国产情色
素人自拍
欺辱凌辱
多人群交
野外车震
学生诱惑
过膝袜
女同性恋
男同性恋
SM调教
抖阴视频
AI换脸
翹臀美尻
贫乳小奶
极品媚黑
人妖扶她
韩国御姐
素人搭讪
国产乱伦
绿帽淫妻
麻豆传媒
杏吧传媒
兔子先生
天美传媒
SA国际传媒
性世界
扣扣传媒
果冻传媒
星空无限
精东影业
葫芦影业
蜜桃传媒
起点传媒
怀旧AV
JIVD
空姐模特
职场模特
国模私拍
福利姬
国产名人
小鸟酱专题
中文字幕
日本有码
日本无码
AV解说
cosplay淫圈
黑丝诱惑
SWAG
偷拍自拍
激情动漫
网红主播
91探花
三级伦理
VR影院
国产传媒
素人搭讪
日本写真
网友自拍
露出激情
街拍偷拍
丝袜美腿
里番漫画
欧美风情
都市激情
校园情事
人妻纵情
风俗伦理
另类小说
武侠古典
长篇连载
【两点之间】(17-
来源:jkun资源站 发布时间:2024-04-01 04:13:00
作者:不详
字数:10732
第十七章五行多水
我赶紧折返回来,推开洗手间的门反手关上,她正坐在盥洗台上咯咯地笑,
两条洁白修长的玉腿兀自来回晃荡,她不知什么时候把丝袜脱了,高跟鞋甩在墙
角,一只立着,一只倒伏在地上。
「走不了啦,只有等到我同事睡觉了。」我无奈地压低嗓音说。
「那怎么办?我肚子好饿哟。」她嘟着嘴。
「都怪你,饿死活该,要不是你不闯进来,要不是你磨磨蹭蹭的,今天也不
会有这么一处。」我一股脑儿把火发在她身上,声音很低但是却很愤怒。
她吓了一跳,怔住了,不再像刚才那样觉得好玩,她脸上青一块白一块,从
盥洗台上蹦下来,抓起白色手提皮包,赤着脚气嘟嘟地就往外走,我赶紧拦腰抱
住。
「我的小姑奶奶,别冲动啊。」我几乎在求她,她的腰好柔软,小腹上没有
一点赘肉。
「我饿了,我要去吃饭!」她再次强调她很饿。
「你说,吃什么,我分分钟给你买回来。」我说。
「真的?」她问。
「真的,我怕你了。」我说。
「那好吧,让我想想。」她昂着头,骄傲地走回盥洗台上坐上去,用手支起
下巴认真地思考着。
「好了吗?」我有点沉不住气了。
「你让我想想嘛!」她生气了,我像被人捏在手里的柿子软了下来。
「红烧肥肠!」她终于下定决心了。
我赶紧闪身出来,低着头就往外跑,经过客厅的时候,舒姐正和那女孩聊得
热火朝天,舒姐叫住了我:「你去干嘛?这么急火火的。」
我心神不定地说:「我去带个饭,肚子饿了。」
「给我也带一个吧,我们也饿了。」她问旁边的那个女孩吃什么,那个女孩
抬起一直低着的清秀的脸庞说:「红烧肥肠。」我感觉她怎么有点面熟。
「那我也来个红烧肥肠吧。」舒姐说,我的天,今天是怎么了,都是红烧肥
肠,仿佛约好的一样。不过也难怪,街边有家「老太婆肥肠」很有名,每天到吃
饭的时分那简直是座无虚席。
本部分内容设定了隐藏,需要回复后才能看到
她扭头像只归巢的小鸟向舒姐跑去,舒姐伸手在她的运动裤裹着的肥圆的的
臀上掐了一下,她尖叫着轻摆细腰躲开了,回头瞟了我一眼,正好和我的目光对
接,我又赶紧把目光转移到别处去了,楼梯口传来们打情骂俏的欢笑声,她们一
前一后的「噔噔」地上楼去了。
第十八章如是听闻
我一直在等着她们睡觉,还好今天她们睡得比较早,我轻手轻脚地向里面的
卫生间走去,推开门,只见胡纤纤靠着墙低着头蹲着,眼睛里含着泪珠,看起来
那么忧伤和颓废,我突然觉得有点对不住她,为了我所谓的面子,把她「囚禁」
了那么久。她抬头看见了我,张开两片性感的嘴唇喜出望外地正要说话,我赶紧
把食指竖在嘴皮上「嘘」了一声,用手指了指卫生间的天花班上,舒姐睡觉的阁
楼就在横梁上,横跨里外两个卫生间,阁楼上她们睡觉前嬉戏打闹的声音清晰可
闻。
她吃了一惊,默默地穿上丝袜,正准备穿上高跟鞋,我打着手势制止了她,
高跟鞋走路响亮的声音,楼上肯定会听得见了。她一脸茫然地站在那里,不知所
措,我拿过盥洗台上的白色手提包放她手上,转身背对着她弯下身子。她犹豫了
一两秒钟,慢慢地趴在我的背上。我双手搂起她的双腿,就往外面走。鼓胀的胸
脯压迫着我的背脊,痒痒的温度慢慢地穿透彼此的衣物渗透到我背上来,让我的
血液慢慢升温。她的短裙盖不住她的大腿,我的手掌隔着薄薄的丝袜,感觉到她
的大腿是那么的软,仿佛要挤压出水来,她把下巴轻轻地靠在我的肩上,吐出来
的热气熏着我的耳根,像玉兰花的香味,弄得我的耳根痒酥酥的。
到了接待厅里,我想把她轻轻地放在沙发上,她赖着不肯下来,我只好连自
己也倒在沙发上。「真对不住……」我小声地道歉。
「今天晚上大清扫,又不用接客,该道歉的是我,给你惹来那么多的麻烦。」
她边穿高跟鞋边说。
「接下来去哪呢?」我问她。
「不知道呢。」她说「耽搁了这么久回去,你老板会打你吧?」我有点担心
地问,我想起了那天晚上那个用纸糊的钢管打女人的男人。
「我是一个人单干。」她阴郁地说,我知道她们单干的往往收不到顾客的钱。
「我送你出去吧?」我看见她站起身来要往外走,我对她说。
「不用了,你电话多少?我来找你。」她掏出电话要记下电话号码。
我报了我的电话号码,她试着打了我的电话一次就挂了,她理了理头发,走
向玻璃门走了出去。听着高跟鞋的声音慢慢地从楼道下去,渐行渐远,我心里禁
不住有些失落,她像一阵秋风卷起的树叶,飘到我这里,又无声无息地飘走了,
我担心她就像陆爽那样从我的的生活中从此消失掉。
我走到前台,馨儿给我发来好几条信息,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是说她已经下
班了,问我在干什么,我回复了,很久没有人回。我看了看时间,都十点过了,
也许她睡了吧。我觉得百无聊赖,便像往常一样,把公司的卷帘门拉下来,回来
把电脑声音关了,打开AV网站点开全屏看起来,一边把裤带松活了一下,把手
插进裤裆里轻轻地安抚着它。外面淅淅沥沥的下起小雨来,风吹过窗外的树叶发
出沙沙的声音。
我看着这无声的活色生香的画面,欧美的靓女正坐在粗大的阳具上起起落落,
表情无尽欢娱,欲望一点点地攒积起来,我想要尿尿。我把画面关了,轻轻而从
容地向卫生间走去,无声无息地掩上门,掏出那灼热的话儿,对着马桶,微闭了
双眼,轻轻地套动。我有时候看着它,心里会泛起一点骄傲的情绪,它在初三的
时候就已经很大了,现在更长了一些。脑海里面出现竟是她的黑色丝袜,她的丰
满浑圆的臀部。正在我沉醉在这无声无息的快感之中的时候,阁楼上传来躯体翻
动的声音,把楼板压得吱呀作响,还伴随着嘤咛的一声低吟。
「好热……」我听见一个声音低低地说。
「脱了吧!」这是舒姐的声音。
「恩……」余淼仿佛梦呓一样的声音游丝一般从楼板的缝隙滑落下来,穿进
我的耳朵,有种致命的诱惑。
「你这骚货,嗯,你有点湿了哦!」舒姐说「讨厌,才没有呢,你才湿了!」
余淼有点前后矛盾地说。
「你用手指试试看,就知道啦。」舒姐挑逗的说。
「啊,真的湿了,有点湿了。你真骚啊!」余淼好像伸手去摸过舒姐的那里
了。
「你带了没有?」舒姐问。
「什么?噢,没带,你用手嘛。」余淼说。
「我不,我要给你舔。」舒姐说。
「不要……坏人。」余淼尖叫起来,声音突然像被硬生生切断了,也许是觉
察到太大声了,怕在前台的我听见了「快点嘛,别装了。瞧你挑逗小宇那骚劲儿,
就知道你很想要了。」舒姐提到了我。
「我哪有嘛?不过你看小宇好色哦,看我那眼神……」余淼说,我在下面脸
都烫了。
「是吗?我怎么没发现,我觉得小宇挺正经的。」舒姐说,这话我听起来受
用,原来我在舒姐心里面是这么一个好人。
「正经?下面都好大一坨,把裤裆都顶起来那么高,要是我是你,嘿嘿……」
余淼低低的笑着说,我早该知道她是这么淫荡的。
「是你怎么了?他就在下面啊,你去啊,让他的大鸟捅死你。」舒姐咯咯地
笑了。
「我才不怕呢,我巴不得,好久都没用过真鸟了,都不知道什么滋味了。」
余淼说。
「那你去啊,你这骚货!」舒姐有点生气了,好像在吃醋一样。
「好啦,不说了。你是我的最爱嘛,男人都是坏人,都是贱人。」余淼柔声
地安慰舒姐,我不知道她们怎么这样痛恨男人。
「嗯,你把腿分开点,好吗?」舒姐说,我想象得出舒姐那急不可耐的样子。
「嗯,那你慢慢往下哦,慢慢往下哦……」余淼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变成
了气若游丝的呻唤:「啊……喔……哦……哦……噢……」伴随着「噼噼啪啪」
的狗舔浆糊的声音,我跟着这淫靡的节奏,握住那鼓胀套动起来,不知道是为什
么,今天特别硬。
「嗯……舌尖再往上一点儿,舔那点,好痒。」余淼有气无力地要求。
「啊……没舔到,再……再往上一点点。」舒姐真的是笨,我恨不得趴在双
胯间的是我,不过也难怪,她们关了灯的嘛。
「不……」余淼哼出了一个长长的咏叹调,仿佛难受得就要窒息而死。
「骚麻批,舔死你,看你还骚不骚?」舒姐压低声音浊重地说。
「我是骚麻批,我要……要……哦……你用力快吸它,好舒服唉,不要停…
…啊……啊……不要停……啊……啊……」余淼的喘息声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大
声,越来越无所顾忌。我知道她快了,飞快地套动着,试图跟上这节奏。
「呜啊……」楼上长长地一声呻唤,我一等待这个爆裂的时刻,它终于如期
而至,一股浓热的精液刷刷急速喷射而出,啪啪打在卫生间洁白的瓷砖上。我从
高一的时候就学会了这该死的发泄旺盛欲望的手段,也曾经在事后莫名地羞愧和
罪恶,但是在大学里从同学的口中,从成人网站上的帖子知道,自渎并不是我一
个人的专利,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二十多岁的男青年来说,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了。
即便我有这样清晰的认识,但是面对自己欲望发泄的终结,我心里还是隐隐地有
着浅浅的羞愧和罪恶,伴随着肉体的疲乏带来的空虚,欲望在悄然减退,道德在
悄然增长,正如此刻的我。我有时候在想,我的身体里住着我的另外两个化身,
一个魔鬼,一个佛陀,此消彼长,辗转争斗,从未停息。
阁楼上在一阵窸窸窣窣的纸张拉动的声音之后,重新陷入宁静,似乎这一切
并不曾真真切切地在我头顶上发生过,那不过是我的幻觉而已,可是我射出的精
液却是实实在在的,正在卫生间的瓷砖上缓慢而有力地划出一条条笔直的印痕,
就像一只笨拙地不会扭动身体前行的长着圆圆的脑袋的白蛇的小蛇,最后像松树
浓稠的油脂一样缓缓地滑到墙角,逐渐变淡变透明,在白色的地板砖上形成一滩
滩水迹,最后连成一大片不规则的云朵状的图形。
我迈着漂浮的脚步走出卫生间,挨到接待厅的沙发上休息片刻,等那自渎带
来的疲累慢慢消退之后,站起身来踏着重重的脚步往卫生间走去,我故意把声响
弄得很大,好让舒姐以为我只是半夜醒来上卫生间,我撒了一泡尿,清洗了龟头,
有用水把精液流在墙壁上的印渍冲洗干净,才出来到办公室里的沙发上盖上毛毯
蜷缩着沉沉睡去。
第十九章黎明时分
天快亮的的时候,我就醒了过来,我已经形成习惯在这时候醒来——因为搞
清洁的阿姨一般都在这个时候来,不用看时间我也知道是七点左右了,外面还是
黑黑的残夜不愿退去。沙发上的的毛毯已经被我的体温捂得暖烘烘的。我伸展着
手脚,藏在毛毯里胡思乱想,试图抓住昨晚上梦的尾巴,可是什么也记不起来,
我侧耳等着阿姨的敲门声。
「嘭嘭嘭……」讨厌的敲卷帘门的声音终于响起,我期待着这声音,并不代
表我很喜欢这声音,甚至于说是很讨厌这种刺耳的声音的——它让我睡不安枕,
只是这是我的工作内容的一部分而已。我不情愿地从暖暖的沙发上下来,趿着鞋
睡眼惺忪地去开门,阿姨那慈祥和善的笑容也缓解不了我心中的怒气,我不知道
她为什么不在白天来打扫,偏偏要选在大家睡梦正酣的时候。我看了她一眼,一
声不吭地折回办公室的沙发上,继续假寐。因为我根本睡不着,我很清楚地知道
此时此刻的我已经无法再睡着了。阿姨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在洗手间里冲洗拖把
的声音,擦玻璃桌发出的叽叽的让人牙龈发痒让人心发狂的声音,拾掇纸张嗤嗤
拉拉的声音,刷刷的扫地声、拖地声……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像无数只苍蝇围
着我的脑袋打转,挥之不去,我把毛毯扯上来盖住头,可是还是隐隐约约地听得
到这些嘈杂的声音,仿佛过了很久很久,终于听见开启玻璃门的吱呀声了,随后
是拉下卷帘门的「哗啦」声,我才从毛毯里探出头来,不知为何,此时此刻,这
些声音显得多么的悦耳。
我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外面的墙壁和树木终于在黑暗中慢慢地显露出
若有若无的轮廓。天快亮了,我的身体也在慢慢醒来,我知道我的身体每天在我
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那匹小骏马都要在内裤里昂首挺胸,奋蹄欲跃,直到最后直
直的的立起不肯臣服,今天早上也一样涨得难受,甚至觉得有点生疼。我伸进手
掌轻轻地安抚着它,我真想对它说:「嘿,兄弟伙,这一个月来真对不住你了!」
我又想起了陆爽的笑容,不知道她现在在干什么,或者那天她出了车祸……我伸
手给自己一个嘴巴,告诉自己不要再胡思乱想下去。
就在我真心对着它默默道歉的时候,卫生间传来「哗啦啦」的打开水龙头的
声音。舒姐不会起这么早吧,她每天都是我下班了她还在高卧不起。我侧耳细听,
好像在洗脸,我想起来了——余淼!现在离下班时间还有一阵子,看蒙蒙亮的光
线,估计也得有两个小时,还是小睡一会儿吧。这样想着,我重又在暖暖的毛毯
中昏昏然了。
迷迷糊糊中听见杂乱的脚步声在接待厅里踱来踱去,还夹杂着衣服裤摩擦的
沙沙声和倒水时饮水机发出的咕嘟嘟的声音,在睡梦里这一切变得那么漫长。脚
步声缓缓朝这边走来,向办公室这边走来,最后进了办公室,到了我的沙发前,
模模糊糊的黑乎乎的一大团影子遮蔽了我的眼帘,这个梦魇我做过很多次,我竭
力地呼喊着、大叫着想醒过来,我知道我在睡梦里。半醒半梦之间看见黑黑的身
影,腰背那么苗条玲珑,步态那么优美,运动鞋踩在木地板上吱呀作响。黑影在
沙发头静静坐下,就在我的头顶上方,久久坐着一动也不不动,我感到了这身体
是有密度和重量的,实实在在的存在着。一只温热的手掌轻轻拂过我的额头,我
终于挣扎着大叫一声醒了过来,慵懒地坐起身来,却被那手掌捂住了嘴巴,我扭
头看见了余淼,她在微微的晨光中莞尔一笑:「吓着你了?」
「有点,你怎么起这么早?」我抚着胸口好让呼吸平静下来。
「我要赶早车上班的嘛。」她低低地说,顿了一下,她说:「你有烟吗?」
我伸手抓下沙发靠背上的衣服,把烟和打火机找出来递给她,她抽出一支衔
在嘴上,把打火机还给我,把头伸过来说:「给我点上,我喜欢你点烟的样子。」
我便把打火机打燃递过去,她还是伸出手臂,手指轻轻地搭在我的手上,使
劲地连吸两大口,缓缓地把烟雾吐出来。我看看外面的晨光,觉得老是也没有变
化,亮不起来,我问她:「几点了?」她说:「七点一刻了,还早呢。」低着头
不说话了,自顾自地吸着烟,烟头闪闪地发着红红的光亮,像暗夜里的星星。
余淼身穿淡灰色棉质宽T恤和橙黄色的运动裤,脚上穿着白色网棉的运动跑
鞋,白嫩嫩的脸庞在微曦中那么耀眼。她抬起头看着外面说:「你有妹子了吗?」
她的到来一直让我有点手足无措。
我说:「没呢,你呢?」我有过,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她吐出一口烟圈淡淡地说:「有过,不想有了!」她的表情有点黯然,看着
不是装出来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有人说抽烟的女孩有很多伤感的故事,我不愿意触碰她
那些过往,沉默着不说话了,她扭过头来盯着我:「你想要吗?」
「什么?」我有点迷茫地看着她眼,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妹子」还是「那个」,
我想确认一下。
她和我乍一目光对接,惊惶地低下头去,天还不是太亮,看不清她的脸究竟
红了没有。
「舒姐睡着的吧?」我把我的担心说了出来。
「不知道,她默许了的,你知道,我们在谈恋爱。」她似乎勇敢了一点,抬
起头来说。
「她不会不开心吧?」我说,如果是谈朋友,吃醋恐怕是难免的。
「我们只做爱……」她的声音有点沙哑了,我不知道她说的我们是指「我和
她」呢还是「她和舒姐。」
「只做爱?」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性和爱是难分难解的,就像我
和陆爽虽然只是有过那么一次露水情缘,可是我觉得我真的爱上她了,老是忘不
了她的影子。
第二十章爱外之外
她在我头顶俯下身来,用纤纤细细的两个手指把烟取下来递在我的唇间,我
不可抗拒地张开唇衔着燃了半截的烟。她伸过手来摸我的头发,摸我的额头和脸
颊,伸进我的领口,手指在我的胸膛游移。我支撑着上身的手酥酥地软了,歪着
头倒在沙发上,那只现实的手,现实的手指穿扫过我的后背,在宽宽的肩胛骨上
轻轻地按压着,在我的脊背上颤抖地摩挲着,她温热手掌上的颤抖蔓延到了我的
整个身体。
她站起身来,我翻身仰面躺着看着她,在外面泻入的淡淡的光照中,她开始
脱裤子,一切看起来那么顺理成章。她的动作不急,但是也没有犹豫,连带内裤
一起往下褪去,裤子和鞋卷着一团落在地板上。在早晨细碎迷离的微光里,一副
玲珑丰腴的女人的身体,光着下身坦然而宁静地立在木地板上,浑身洋溢生命无
尽的活力。海藻般的长发从头顶披散在肩上,大小适中却结实的乳房在宽大的T
恤里颤巍巍地静默着。两条大腿颀长而流畅,柔韧而结实,丰润而微翘的的臀泛
着微微的白光,两腿之间性感诱人的毛从小小的一片,素淡而雅致。
我呆呆地看着她,不知不觉手中的烟已经燃尽,长长的烟蒂终于不堪重负,
累积的烟柱落在地板上软塌塌地碎了。她走过来弯下腰腰揭开毛毯,一个一个解
开我衬衫的钮扣,熟练地拉开我的皮带,从容地脱下我的内裤,露出我那欲望的
神经。我弓起腿让她容易往下拉。她拉到腿弯处便停住了,穿着宽大的T恤跨上
狭窄的沙发,趴在我身上,亲吻着我的额头,脸颊,找到我的嘴唇,撬开了我的
牙关,她的舌从两叶温婉的唇中伸出来,伸进我的唇间,撬开了我的牙关进来了,
她找到了我的舌,我也寻找到了她的舌!两人鼻唇间灼热的气息急促地蔓延开来,
都张着鼻翼用力呼吸,都热烈吮住彼此的舌苔,交缠着不放松。
我的双手不安分地滑向她的臀部,把她的T恤往上撸,她直起身来把T恤从
头上脱下,她并没有穿乳罩,那一双光滑白皙的乳房像兔子一般跳脱而出,玲珑
光滑的上半身毫无顾忌地袒露在逐渐明亮起来的晨光里,暗红的乳头追逐着我的
目光。我的手指在那圆润的胸乳上摩挲,就像触摸在两只天鹅绒圆球上,艳红的
樱桃饱满欲裂……她的呼吸急促起来,似乎血管里的血液沸腾了,仰着头伸长脖
颈朝着天花板吐气。白皙的手臂反撑在我的膝盖上,用力用力的把胸部挺向我,
挺向我……我甚至感觉到了她的毛从,就在那里茸茸地一团,把我的小腹蹭得痒
痒的。她用膝盖支撑着身体,抬起屁股,留出多余的空间。双手从后面摸索着攥
住我的阳物,阳物已经硬硬地勃起,如石杵一般硬。
她轻轻抓住我的蘑菇头,一声不响地抵在温暖而湿润毛丛之下,要将它导入
自己体内,那蘑菇头好像被吸进去一样缓缓进入她体内,我感觉到滑滑的肉缝渐
渐地吞没我了我的燥热,如羊水一样软乎乎暖融融,转眼之间将我的意识包裹起
来,地包拢起来,这种感觉让我心慌意乱。然而一切都像奔跑的列车,由她选择,
由不得我选择,我也来不及选择,我无法遏制列车奔跑的势头。她像波浪一样扭
动腰肢,她变幻成臀部转圈的方式,像推磨一样旋转着,海藻般的长发在她完美
的肩头不安地跳来跳去。我被一点点地吞入魔鬼的沼泽,窗外的树枝和石砌的潮
湿的挡墙变得暖融融的,就连旁边的办公桌和文件柜也变得迷迷蒙蒙的不清晰起
来,时间也在不确定地左右流移。我唯一能确定的是,我的阳物坚挺而鲜明地在
那热带的雨林中前进后退,摇摆不定,尖端传来搅动的快感,爱液沿柱而下,打
湿了我的毛从和睾丸,流到下面的沙发上,毛毯早已滑落在地板上,羞涩柔软地
缩成一团。我们都不敢发出太大声,她仰着头低微地嗫嚅,发出喃喃的颤动的声
韵,夹杂着欢快的音调。阁楼上的舒姐不知在酣睡还是在倾听,虽然她说舒姐是
默许了的,可是如此隐秘的运动,我们还是有所顾忌,是啊,不管怎样,这是一
件很隐秘的事情,很隐秘,我们从小就知道。
不知什么时候,天色已近无法扩展它的亮度。过了良久,她突然更加疯狂地
扭动着身体,伴随着她的花房一阵阵抽搐。一股热流从遥远的地方醒来,像夏天
的雷一样低低地近了,像岩浆一样喷薄而出,股股暖流兜头淹没了我。我仍就不
愿停歇,就像一条饿极了的狼,用欲望的而坚硬的舌贪婪地舔吮着这琼浆玉露,
我很快把憋屈了很久的欲望汁液射出,在她体内一次接一次猛射,无法遏制。她
的内壁在一阵一阵地收缩,她蜷缩着通透莹润的足趾,仰着头长嘘不已,那里在
温柔地收集我的精液,仿佛要把它们吸到另一世界里去。我寂寞的骏马,终于找
到了归宿。
余淼的身子已软得像一滩泥,娇慵无力地软塌下来,趴伏在我的胸膛上,满
脸汗津津地,轻轻地弹弄着我的乳头,她懒懒地说:「想不到你深藏不露啊,看
不出来啊」,我小心翼翼地梳理着她的海藻般的长发,我没有说话。我不想告诉
她,我虽然只和一个女孩睡过觉,可是我们睡了两年,这两年是我一生中最值得
回忆的岁月,没有压力,远离尘嚣,远离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一生已嫌太久,
即便如昙花一现,也足以温暖我寂寞的一生。
她抓起掉在地上的毛毯盖在身上,扭身在沙发靠背上拿下烟盒,抽出一支烟
点燃,把烟雾喷在我的面上,我不得不憋了起眯起眼看着她。
第二十一章无不伤心
她说:「老舒干过你吧?」
我第一次听人叫舒姐做「老舒」,我摇着头说:「没有。」
她不相信地说:「我才不信呢,你们经常两个人单独在公司里,还是晚上。」
我笑了:「真的,舒姐很凶的,像个母老虎,谁敢惹她?」
她吸了一口烟,摇着头说:「那是她另外的一面啦,她很温柔的,你有没有
想过干她一回?」
我头摇得像博浪鼓似的:「没有,我从来没这样想过,她那么瘦,勾不起欲
望来。」我说的是事实,太瘦的女生,摸上去全是骨头,想想都有点恐怖。
「才不呢?女人是穿起衣服看起来瘦,脱了衣服就有肉了,龟儿豁你。」重
庆人说「龟儿豁你」相当于书面语「我不骗你」。
我有点不相信:「是这样的吗?」
她哈哈笑了:「你说是不是这样的?我和她睡过,可骚了,水又多。」
我来了兴趣:「那她不找个男的谈恋爱?」
余淼突然间显得有些伤感:「你不知道,她耍过两个男朋友,第一个耍了三
年,第二个耍了两年,最后都分了,她是很用心的那种人,这两次伤她可够深,
第一次失恋的时候茶饭不思,呆呆地一个月,足足瘦了二十斤,别人都以为她脑
袋坏掉了,没想到一个过了月就去上班了,一上班就上到现在,一个人呆在那个
阁楼上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听舒姐说起过她的故事,听起来是这么传奇,想不到她凶悍的外
表下柔弱的骨子里竟曾是这么个痴心的女孩,她把烟放到我嘴里,我吸了一口,
把烟夹在手指上问她:「那第二个呢?」
她幽幽地说:「第二个是在公司里面谈的同事,谈了两年,都见过家长准备
结婚,那男孩突然辞职不干了,从此不知所踪,这次舒姐彻底地绝望了,每天就
喝酒,到现在都是这样。」她的神情很伤感,仿佛失恋的是她自己而不是舒姐。
这个我知道,舒姐经常出去喝酒,醉醺醺的回来,有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也把
罐装啤酒带回公司来一个人自己喝。
「那你也喝酒吗?」她好奇地问,把烟从我手中拿过去放在樱桃小嘴里。
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不知道,看过《东邪西毒》吗?里面欧阳锋说:
你知道喝酒和喝水的区别吗?酒,越喝越暖,水,越喝越寒 ,这话不对,至
少在我身上不对,我不论和什么酒,身上会越来越冷。冷得发抖。」
她扑闪着羚羊般美丽的大眼睛说:「那挺奇怪的呀,那你岂不是很容易醉?」
我说:「是这样的,但是有时候不一样,有那么几次,我能喝很多而不会醉。」
她更好奇了:「你真的很奇怪耶,你干过几个女孩?」
她突然转换了话题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我从她的嘴里拔出烟来狠狠地吸了一
口说:「一个,就一个,在我十六岁的时候。」
她嘴巴张大得合不拢来:「那么早就开发了呀,你是不是天生就这么厉害?」
我脸上被她说得烫了:「哪有呢?刚开始还不是一样的,银样镴枪头,中看
不中用,我们在一起两年,干了两年。」
她眼睛瞪得更大了:「哇,那你会很多姿势啰?」三秋狗「会不会?」
我哈哈地笑了:「我知道,但是没用过,那要男的阴茎够长才做的到。」
她伸手握住我疲软的下体说:「我觉得它够长的啊,量过没有,有多长?」
我也不知道我的算不算长,我只是在火车站看过那个死变态的金针菇,还是
有些自信,我说:「量过的,快十七厘米了吧?」
她用手比划了一下看看十七厘米有多长,尖叫起来:「我的天哪?这么长啊,
要不我们下一次试一试 三秋狗 吧?在电影里看见过,我和老舒都不相信是真
的。」
我说:「好啊,我也很想试试这个姿势呢?以前和女朋友试了几次,没有做
成。」
她歪着头说:「你想干老舒吗?说实话。」
我犹豫了一下,我并不是不愿意,我只是觉得作为同事,如果做了以后怎么
面对,而我口里说出来的却是这样的话:「那要看她的意思了。」
她信心慢慢地说:「这事你就不容操心了,包在我身上,到时候等我好消息,
我想她会喜欢你的芽儿的,她那么骚,每天就想着干呀干的。」重庆话把男人的
那里叫做「芽儿」,生命之芽,我觉得挺形象的,只是把女人的那里叫做「麻批」,
这让我有点费解,不知所云,也许是说那里的颜色是黑麻麻的吧?或者是说能让
人痒麻麻的或者自己会痒麻麻的,重庆话里把「非常痒」说成「痒麻了」。
我说:「你呢?耍过几个朋友?」
她神色显得有点黯然:「其实我和老舒差不多,或者比她更惨,还说这些干
嘛呢?都过去了,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人,你也是这样,对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句话,我觉得男人女人都有善良的人和不善良的人,
至于说到我,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是属于好人呢还是坏人,一时噎住说不出一句话
来。
她见我不说话,也就不再问下去了:「你的那个她呢?现在没有联系?」
我叹了口气:「她死了,生了疾病,一夜之间……」
她打断了我的话,眼睛里闪着泪光说:「我知道,别再说下去了,好吗?」
烟已经燃尽,她摸着我的脸颊像是在安慰着我,怕我哭起来一样,我早就不
哭了,好多年没哭过了。有那么几分钟,我们都沉默着不说话,她的手机在地上
的裤子里响了起来,她歪过身子去伸长手勾着裤子拿过来,把手机翻出来,趴在
我胸脯上按下接听键。
电话那头确实舒姐的声音:「骚货,你被杵昏了,看看现在几点了,还不去
上班?等会儿迟到了又要怪我!」舒姐像连珠炮似的数落着。
她一点也不甘示弱:「你管我,我就是被杵昏了,你想不想杵嘛,我今天要
请假了,我们出去继续杵,日一天。」
我有些不太喜欢她们这样粗暴的交流方式,好像把我当着一件新发现的有趣
的玩具一样。「你真不去上班了?」我问她。
「怎么不去呢,请假要扣二百五十块钱的,不划算,你不会是搞安逸了,舍
不得我了吧?」
她调侃着说,一边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焦急地尖叫起来:「我操,要迟到
了,都快九点了!」她倏地翻身下了沙发,拾起地板上凌乱的衣服忙乱地穿起来。
我点燃了一支烟抽上,看着她急躁地扭动着苗条雪白的身子,看着有种别样
的诱惑。「你电话多少?」我问她。
「你啊,是饥渴了吧?」她的衣服穿好了,抬起头来甩了甩头发,把头发扎
在脑后,向我伸出手来说:「手机。」
我把她的手机翻出来给她,她接过手机摇了摇头:「你的。」我到处找我的
手机就是找不到,我翻下沙发爬在地上往沙发地下看。
「快点啊。」她在后面焦灼地跺着脚说,还好终于在沙发脚边找到了,我伸
手进去掏出来递给她,她噼噼啪啪在上面按了几下递给我:「诺,好了,想我了
就打给我吧。」她像个热恋的情人那样笑起来,嘴角微微向上扬起,两边脸颊上
愉快地浮上两个小小的酒窝,说完飞快地地外急急地走了。
【未完待续】
若本站收录的文章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删除侵权内容!
警告:本站立足于美利坚合众国並遵守美利坚法律服务于海外华人,谢绝中国大陆地区访问!
如您未满十八岁或当地法律不允许之年龄、亦或者您对本站内容反感,请自觉离开本站!
寻艳回首 :https://xunyanhs.github.io
聯絡: [email protected]
如您未满十八岁或当地法律不允许之年龄、亦或者您对本站内容反感,请自觉离开本站!
寻艳回首 :https://xunyanhs.github.io
聯絡: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