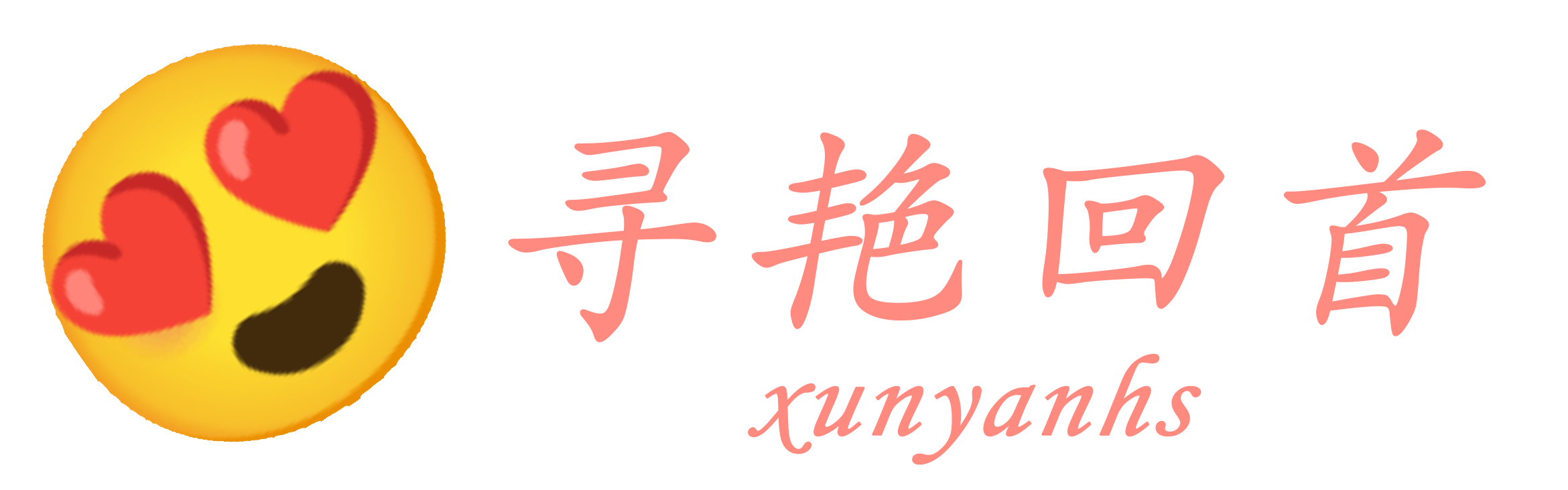视频
网红黑料瓜
巨乳姨妈
人妻熟女
强奸乱伦
欧美精品
萝莉少女
口交颜射
日本精品
国产情色
素人自拍
欺辱凌辱
多人群交
野外车震
学生诱惑
过膝袜
女同性恋
男同性恋
SM调教
抖阴视频
AI换脸
翹臀美尻
贫乳小奶
极品媚黑
人妖扶她
韩国御姐
素人搭讪
国产乱伦
绿帽淫妻
麻豆传媒
杏吧传媒
兔子先生
天美传媒
SA国际传媒
性世界
扣扣传媒
果冻传媒
星空无限
精东影业
葫芦影业
蜜桃传媒
起点传媒
怀旧AV
JIVD
空姐模特
职场模特
国模私拍
福利姬
国产名人
小鸟酱专题
中文字幕
日本有码
日本无码
AV解说
cosplay淫圈
黑丝诱惑
SWAG
偷拍自拍
激情动漫
网红主播
91探花
三级伦理
VR影院
国产传媒
素人搭讪
日本写真
网友自拍
露出激情
街拍偷拍
丝袜美腿
里番漫画
欧美风情
都市激情
校园情事
人妻纵情
风俗伦理
另类小说
武侠古典
长篇连载
【乱与虐】(十二-十三)
来源:jkun资源站 发布时间:2024-04-01 04:13:02
(十二)
一天夜里,后半夜,鸡还没叫头遍的时候,全镇突然被一阵尖历的哨子声惊
醒,接下来便是孩子哭、女人叫、鸡飞、狗咬,砸门声,喝斥声传遍了我们这个
古老的集镇。
没出意料的,刚刚穿好了衣服解完大小便的妈妈被突然闯入的民兵捆绑着带
走了。
我悄悄走到大街上,左右邻居们都在三个一群五个一堆的小声的议论。在这
议论中,才知道了我们县里破获了什么「国民党地下挺进支部」的反革命大案。
我象是鬼子进村一般,悄悄地走到公社大院,只见高高的围墙下面,黑压压
跪了一大片的「国民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有,足有五十多个,全都五花大
绑着,跪在铺了煤渣的地面上,等待着刑讯。里面几间大房子里,正不断传来受
刑者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
找了半天,没有见到跪着的人群中有妈妈。我怕了,妈妈一定是在受刑。我
胆战心惊地朝着两处刑讯的房间走去,那两间门大大地敞开着,似乎有意让人们
观看。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正反背着双臂寒鸭凫水般吊着,几个造反派正抡
动着沾了水的皮鞭拷打着。
「多久参加的?」
「解放前……1944年。」实际上那人不过四十岁上下,1944年还没成年呢。
「你的上级领导是谁?」
「是……蒋介石。」连我都不相信,蒋介石会认识这么一个远在冀中的出身
富农的七十年代的农民。
「他给你什么指示?」
「反攻大陆……复辟资本主义……」
我又往另一间发出嚎叫的房间去看,房间里,一个经常偷偷在集市上卖炒瓜
子的女人正在坐着老虎凳,一双嫩脚下垫着四块砖了,一个壮汉却仍然在抬着她
的脚,试图把第五块砖垫入。
「哎哟……受不了了呀,我全承认……亲爷爷别垫砖了呀!」
「你偷偷卖瓜子,是想干什么?」
「我承认……投机倒把,传递情报……搞复辟……」
「你和谁接头?」
「国民党……蒋介石……」
「你的发报机藏在哪里了?」
「丢河里了。」
「带我们去找。」
那女人被从老虎凳上解下来,带走了。后来得知,就在河边指任她丢弃那并
不存在的「发报机」的地点的时候,趁看押她的民兵不备,带着捆绑着她的麻绳
和心灵上无尽的屈辱,满身伤痕的她跳进了滚滚的河水。
正在一间房一间房地寻找着,突然,几个穿着军装带着盒子炮的人押着一个
五花大绑的人走来,走近了,才发现,这正是林大可。林大可显然已经被拷打的
十分严重,高高的个子勾楼着,已经无法挺起那标准的军人姿态,一支腿似乎受
了伤,一蹦一蹦地被两个武装人员押着。我赶紧躲进一个空房子,好在没有人注
意我,他们走了过去。
找了半天,终于在一片原来用作打麻绳的工具房里看到了妈妈。房子里跪了
七八个人,全都脸朝着墙壁,不过从背影,我当然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妈妈,不过
此时的他们还没遭遇到酷刑的折磨,只是全都五花大绑着。
「偷看什么?想进去吗?」
是卫小光的声音,只见他正背着那支从不离身的日本造的王八盒子,趾高气
扬地朝我走来。我想走开,向着一边迈步,却不小心踩空了脚,歪邪着向一边倒
去,就在我将要摔倒时,正好落到一个人的身上,定睛一看,却是郭二麻子,吓
得我刚要说什么又不知说什么时,郭二麻子却一把推开我,象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似的,对着卫小光说道:「他妈的还是没找到,你找到他没有?」
「没有,不过你看,这双鞋好象是他的,在河边捡到的。」
郭二麻子看了看那双布鞋,骂了一句,「自绝于人民,他妈的,便宜他了。」
不知道他们说的是谁,应该是想抓而没有抓住的某个人吧。
他们全不想理我,我便偷偷地溜开,迎门一个桌子边,一位年近四十的军人
正对他身边的人说着什么,见郭二麻子走来,便大着嗓门说道:「行啊老郭,这
次咱们县算立了大功,你是头功哇!」
郭二麻子腰里别着盒子炮,对着那军人说道:「这是卫小光同志,原来是‘
全无敌’的副指挥,就是他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这才挖出了林大可这个暗藏的
阶级敌人。」
后来才知道,那中年军人,正是我县群专组织的总指挥,驻公检法军管小组
的组长,原县武装部的副政委,姓魏,他与郭二麻子早先是战友,有着密切的关
系,这次全县搜捕国民党,就是他指挥的。
这次清查,全公社有好几个国民党被酷刑折磨致死,也有好几个无法忍受酷
刑而选择了自杀,整个古镇笼罩在一片死亡的恐怖之中。
我躲在不远处观望着,终于看到了魏副政委在郭二麻子的引领下朝着关押妈
妈的屋子走去。大院里很乱,看热闹的群众就象今天追逐李宇春的粉丝般涌动着,
我也朝向那间屋子移动过去。
妈妈和另外跪着的七八个男女被命令站立起来,朝向工作组的大员们低头并
成一排,魏副政委走过去,近在咫尺地从排头向着排尾踱步,一个一个地打量着
几个等待命运判决的「国民党地下挺进军」,当走到其中的一个女人面前时,他
将原本背着的手伸出,托起那女人的下巴,将那女人的脸高高地托起,但很快又
放下。下一个是男人,他重又背起手。待走到妈妈面前时,却又将倒背着的手伸
出,象刚才托那女人一样捏住妈妈的下巴,将妈妈的脸托起来,却并没有那刚才
那样快速地放下,而是左一扬、右一扬地将妈妈的脸扳过来扳过去地看着,又用
另一支手撩开遮挡住妈妈大半个脸的长发,重新将妈妈的头转动着,妈妈屏住呼
吸,象个玩具般任他摆弄着、端详着,眼睛不敢看他,只是看着自己的鼻子,长
长的睫毛便覆盖住自己的双眼。魏副政委用一支手的拇指撩动妈妈的眉骨处,迫
使妈妈将眼睛向上张开,可眼睛尽管已经张大,却仍然不敢看那淫邪的脸,而将
眼珠朝向斜下方看去。
「叫什么?」魏副政委声音不大地问道。
「郑小婉。」妈妈颤抖着声音回答。
「你什么问题?」
这一下把妈妈问倒了,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呢,可不回答是不行的,于是妈妈
回答:「反革命……破鞋……」
「破鞋?」那魏副政委转过脸,对着郭二麻子,问道,「谁搞的?」
郭二麻子回答道:「和好几个人搞过。」
那副政委放开了一直捏弄着妈妈的手,仍旧看着郭二麻子,小声地,「哼哼!
没有你吧?」声音很小,但屋子里的人却全都听得清楚。郭二麻子现出调皮的坏
笑,与副政委对视了一下,没有答话。
「毛主席教导过我们,对于阶级敌人要毫不留情,但对于他们中的某些人,
也要注意方式方法」,说到这里他停顿住,看着郭二麻子,怕他不理解地看着郭
二麻子,「嗯?」
郭二麻子象是完全理解老战友的心思,赶忙表态:「首长放心,毛主席的话
我们理解,首长的话我也理解。」
魏副政委不怀好意地看了一眼郭二麻子,二人会心地微笑了一下。
到了晚上,出人意料的,妈妈被放了回来。她回来后便要我到别人家去玩,
等她喊我再回家,要是不喊我,就住别人家。我隐隐约约猜出了什么,便赶紧着
拿了一块冰凉棒硬的玉米面饼子啃起来,妈妈心疼地给我往饼子里抹了一块猪油,
又洒了些细盐,便催促我快走。
我走出了院子,看到那个魏总指挥正和郭二麻子往我家中走来,便趁他们没
注意到我时,一闪身躲进了门外的茅厕中。
我蹲在茅坑里,外面的脚步声就是郭二麻子和他的战友总指挥的,只听郭二
麻子小声地说道:「老首长……」
「什么他妈的老首长,你别来这一套。」这是魏副政委的声音,口气中并不
是气愤,反倒显着亲切。
「呵呵!老战友,呵呵!我跟你说,一直没给她用刑,就是给你留着的。郑
小婉这娘们,干起来会叫的很,呵呵!你上了就知道了。」
「保险吗,别传出去,传出去让人知道了就不好了,要是让阶级敌人知道了
更不好了。」又是那魏副政委的话。
「哎你放心,我给你找的,你还不放心吗?谁敢说?郑小婉敢说?她不说谁
知道,放心,一会我把她儿子关起来关一晚上,你好好抱她睡吧,哈哈!」
果然,在我刚刚到一个小伙伴家门口时,背后便传来了郭二麻子的喊叫声,
我被他关进了公社的一间屋子里,既没人审也没人问地直关到天亮,才放我回家。
到了第二天,公社大街上仍然在抓人,成分高的、解放前与国民党有瓜葛的,
都给抓了起来,连被国民党抓壮丁后又被解放参加人民解放军的,也全都被抓了
来。
待我回到家中,奇怪的是,妈妈并没有被捆走继续审问,也没有下地参加农
业劳动,而是象什么也没发生般的对房屋进行着大扫除——在这个时候,她竟然
有这份心思,这比看见太阳从西边出来还让我感到不解。
「妈你怎么……?」
妈妈很平静地看了看我,「我洗的炕单一个人拧不动,过来跟我一起拧干我
好晾晒。」
原来,是魏副政委亲自安排的,要妈妈在家里写反省材料,不用再去公社大
院挨批受审,也不用再去生产队的田里干活。可从我到家一直到天黑,妈妈除了
将房子象过年时那样收拾的干干净净,将铺炕的被单洗的干干净净,又将我的和
她自己的衣服洗的干干净净,她一个字的反省也没写。
因为这次搜捕国民党特务没有涉及到我这个年龄的,全天我便无所事事。
到了晚上,我正西屋里玩弄着一支新捡来的弹壳,研究它属于什么枪的子弹
壳时,屋门传来重重的脚步声,我正要出去看时,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他妈
的洗干净了?」这就是那个魏副政委,很快的,他不等妈妈回答,便又说道,
「今个好好审审你。」说的是审,但话语里却听不出半点以往那种肃杀的火药味,
反而象是一种十分轻松的玩笑似的。
妈妈迎了出去,低下头,轻声说道:「破鞋郑小婉接受总指挥批斗。」
奇怪的是,妈妈的话,内容虽然都是以前遇到造反派时的内容,但口气里却
也同样显着十分的轻松,甚至玩笑。
「嗯……这他妈的才乖,来来,我先检查检查你这里面……」
「啊!」妈妈的一声尖叫,随即便是明显撒娇的声音,「哎哟!你的手好大
劲……」紧接着便小声地,「孩子在屋里……」
魏总指挥稍稍压低了声音,但依旧比别人的声音响亮,对着妈妈说道:「你
跟我说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叫什么兰?我今天怎么没看到?」
妈妈回答:「鹿一兰。她是……」
「行了,记着了」,魏政委打断了妈妈的话,「弄死她还不跟弄死个蚂蚁似
的,到时给你报了仇,你得怎么报答我?嗯?哈哈……」
从门帘的缝隙中看到,妈妈已经被他用力地揽在怀中,小声地回答:「首长
……把她打倒别再欺负我就行了,可别弄死人呀!」
趁着魏副政委搂着妈妈进了东间屋子,我悄悄地溜了出来。
又是一晚上我没回家,不过这次是在二嘎子家住的。
天亮了,在二嘎子家吃了一块南傍国面贴饼子和一碗南傍国面粥后,我又溜到了
公社大街上。因为抓捕反革命,生产队没人组织劳动了,学校没人组织上课了,
就连合作社也关门了。而因为什么组织全都散了,这几天也就没人再管我们这些
半大的孩子们,于是我们便四处地闲逛,主要是看抓捕反革命了。
随着看热闹的人们,我又转到了公社那处大院里来。在这里,我看到了昨天
没有看到的鹿一兰,不过她仍然没有象其他四类那样被捆绑,而是紧紧地跟在卫
小光的身后,提了一个暖水瓶给工作组的人们倒茶。那个坏蛋副政委走进了院子,
站住脚,叉开两腿,倒背着手,冷冷地看着这个穿的远不如往日那么高调的女人,
半晌,才低沉着声音,虎着脸,对她叫道:「你,过来。」
鹿一兰转身走到魏政委的面前,看到他那张脸,全身极不自然又纯粹下意识
地立正,脸上说笑不是笑说媚不是媚的冲着他叫了一声:「首长。」
魏政委直直看着她,「你就是那个利用学唱样板戏歪曲破坏阿庆嫂革命形象
的?」
听到这话,原本还强控制着自己的鹿一兰再也无法禁止住自己的抖动,好的
双腿使劲并拢在一起,「我……我……」我了半天却不知该说什么,原来的抖动
并不因为双腿的并拢而减轻,到象是变成了合力似的更加颤拌起来,连向前倾斜
着的上身也开始发抖了。
魏政委突然大喝一声:「捆起来!」
于是,几个如狼似虎的工作队员,三下五除二便将鹿一兰五花大绑。
「首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我……」
「借唱样板戏的机会,用淫秽下流的色相歪曲地下革命者阿庆嫂?反革命之
心不死呀!哼哼!你的干爹都是谁?他们在台湾怎么给你下指示的?老实交待出
来。」魏副政委严厉地问道。
「当当」两声枪响,一个「国民党」在我身后的大院子里被枪毙。
枪声震的所有的人都不敢出声,没有出现电影里经常出现的尖声喊叫,没有
人哭,甚至连树上蝉鸣也一下子全都停止了。
几个社员将那脑袋上还在往外喷血的死尸拖了出去,再回头时,鹿一兰已经
软软地坐在了地上。
卫小光没有保护好鹿一兰,昨天还伪装革命妄图逃避打击的她一下子被打倒
成了国民党反革命。
连续三天,那姓魏的天天都到我家来,有时晚上来,有时中午也来,但都呆
不久,一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后便走,他是总指挥,事多。
妈妈仍然没有被提审,也仍然没有参加社员们的劳动,一连四五天,天天在
家反省,却一个字也没写过。
这天中午,妈妈闲的没事,便将院子里种的几架豆角收拾了一下,摘了很多
的豇豆,那豇豆长长的嫩嫩的,妈妈双手抓住,正要往屋子里走时,邻居的赵大
婶正好从矮墙的另一侧出现,于是妈妈便走到墙边,隔墙举起那一大掐子豇豆,
对着赵大婶笑着说道:「四姐,刚刚摘的豇豆,太多我吃不了,您拿去吃吧。」
没想到的是,一向友善的赵大婶却突然象是被蜂蛰了一般地高声叫起来:
「呸!破鞋!看来斗你斗的少了,不要脸的!」
妈妈举在半空中的双手一下子僵在了那里,人也整个地木了。
赵大婶却并不解气,又叫起来:「离我远点,我嫌你脏。」
妈妈这才开始又动作,低着头,退了几步,然后快速朝着屋子走去。
我站在院子里,没有听到妈妈的哭声,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哭,呆了好半天,
才犹豫着也回到屋子里。
可我刚刚进屋,正想跟妈妈说什么时,没想到的是,赵大婶却急急地走了进
来,妈妈仍然象往常那样站立起来,这或是出于礼貌,或是出于被管制对象见到
贫下中农后必须的动作。
赵大婶一把抓住妈妈的手,「姐姐给你陪个不是,刚才我话说的太冲了,别
恨我呀!唉!也不怪你,这年头谁敢不从他们呀,别说你一个四类了,就是贫下
中农,也不敢得罪他们呀!」
赵大婶的话,在村子里有一定代表性,但并不全是,在村子里,我就听到有
人议论,说哪个地主家的媳妇,因在挨斗时让人摸了奶子,回家就上了吊,说哪
个富农家的姑娘,挨斗时让人扒了鞋摸了脚,没回家就投了河,说这叫女节,说
一个女人这样让人玩弄就应该去死。后面便说到妈妈、说到那个姓魏的副政委,
话也就很难听了。
姓魏的副政委去县革委会开会,要开两天。晚上八点多钟,因为既没有电影,
也没有批斗会,戏匣子也只有少数的几户人家才有,缺少娱乐的社员们便早早地
钻了被窝。我和妈妈也一样,铺好了被窝,妈妈借着煤油灯跳动的火花偷看一本
苏修的反革命的小说《第四十一个》,我也睡不着,戴上矿石耳机,收听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的长篇小说连播《金光大道》。
就在这时,一点声音也没有的夜晚,我家的外屋突然有人敲门,声音很小,
但因为我家没养狗,屋外又十分地静溢,这细小的敲门声仍然十分地清晰。
听到这声音,妈妈连忙将那反动小说藏到墙柜后面的一个盛满了中药渣滓的
破木桶内,然后才下炕,打开了外屋的门。
一个女人一下子闪进门来,象是作贼似的回头张望了一下,看到的确没人盯
梢,才赶紧关好屋门,一下子抓住妈妈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道:「郑姐,他们
要送我去县群专队,姐姐您救救我吧!」
我和妈妈都惊呆了,好半天,才认出这女人原来竟是鹿一兰。她所说的群专
队,是一个专门的斗争组织,那年头谁听到这三个字,大概就跟汪伪时期听到魔
窟76号或是听到二战时德军集中营一样吧。
不等妈妈说话,鹿一兰又说:「那天我帮助他在梨树窝棚里给老田家的女儿
破处开疱的事……还有,那天在学校会议室我和郑姐您一同招待县里来的齐主任
的事我也都没交待……还有那天我让林校长……这些您别说呀,只要您也别说出
来,就没人知道……」
「行了」,妈妈已经听懂了她的意思,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说道,「我
又不是群专队的,你跟我说有什么用?」
鹿一兰开始变得吞吞吐吐,「只要……只要魏副政委说不让我去……就行。」
妈妈脸色一下了变了,鹿一兰偷偷看到了妈妈脸色的变化,却仍然不放弃地
继续求道:「我真的怕呀,到了那我就活不出来了,您救我呀!」
她的话使妈妈想发作而又找不到词句的处境得到缓解,便不再纠缠她刚才的
话,反而象是找到了某种得以骄傲的资本,直直看着鹿一兰,然后反头高高地向
着一边扬去,冷冷地,「我凭什么?」
妈妈面无表情、或者说一副冰冷表情地看着她,没再说话。
鹿一兰停顿了一下,然后缓缓地、缓缓地,跪了下去,「郑姐……我不知道
该说什么了……我不是人……」
妈妈看着脚下的鹿一兰,还是没说话。
鹿一兰抱住妈妈的腿,「您啐我、煽我,解解恨吧。」
「你出去,出去,别把他们招到我这来。」妈妈依然冷冷地说。
鹿一兰不走,又说了许多可怜的话,才离开了我家。
(十三)
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全公社一下子变了天,「全无敌」被打倒,「从头越」
执掌了革命造反的大权。
用郭二麻子的话说,这才只是革命成功的第一步,要清算「全无敌」的反革
命罪行,特别是要彻底批倒批臭林大可一帮子人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还有很多
的工作要做,还要一步一步地走。他们制定了先外围后核心、先易后难的斗争方
略,并按步就班地开始了执行。
他们决定先从连胖子入手,因为这连胖子,受尽了林大可的欺辱,心中的仇
恨是可想而知的,另一方面,连胖子胆子小,只要稍加威胁,便不怕他不招,于
是,在一个深夜,连胖子被抓到郭二麻子的司令部,位于一片密林中的古城堡里,
没到半夜,吓坏了的连少华便全部招供了。
有了这些把柄在手,郭二麻子开始反攻了。第一着,先拿林大可最灸热的姘
头鹿一兰开刀,于是,曾经的「全无敌」三号人物,出身本来就有问题的鹿一兰
一下子从整人斗人的革命闯将变成了专政的对象。在连续几天没黑夜没白天地酷
刑审问之后,鹿一兰不仅什么全招了,而且郭二麻子们事先编造好的笔录也一一
全认了。
在准备工作做到家以后,一场专门针对连大肚子与鹿一兰搞破鞋的批斗大会
召开了。
连大肚子,就是鹿一兰的公爹,连少华的父亲。这是一个十分封建保守的家
庭,尽管鹿一兰风骚无限,但在连家,绝对是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可不知为
什么,连左右邻居打死也不相信的,连大肚子和儿子媳妇一家,却全部交待了翁
媳之间的扒灰事情。
大会由卫小光主持,公布完了二人扒灰搞破鞋的罪状,便是群众发言,可这
事不能没有旁观者呀,于是便动员了鹿一兰的丈夫连胖子上台发言。连胖子显然
是做了充公的准备的,上得台来,使劲地低着头,完全按照郭二麻子卫小光他们
事先写好的稿子,一句一句地念下来,把他如何收工回家后看到媳妇正在爸爸的
腿上坐着,如何在睡到半夜时发现媳妇钻进了爸爸的被窝,如何在与鹿一兰做爱
时被鹿指责还不如一个六十岁老爹的鸡巴长的粗大等等交待了一遍。当然,按照
我们公社的惯例,每揭发一个事例,便点着名地审问一次自己的父亲或媳妇,二
人也照例地低头认罪承认所揭发的是事实。
之后是连大肚子认罪,跟儿子说的完全一样,几乎就是一字不差。
再之后是鹿一兰认罪,也跟前边的父子俩说的完全一样,什么时间,什么地
点,怎么勾搭上的,谁在上面,谁在下面,谁都说了些什么话,中间换了什么样
的姿势,一点不差,就跟今天流行的复制粘贴似的。
没有人怀疑真的假的,群众照样报以激烈的口号和大声的哄笑,三人的发言
每每被群众的怒吼与哄叫声打断,其被打断的频率比***九大时毛主席的发言时
被打断的频率还要高。
批斗会后是游街,连大肚子有伤,走路困难,于是大会主持人提前想好了办
法,要他的儿子连少华用手推车推着他。因为搞破鞋的男女是要用一根短绳子连
接着拴在脖子上的,于是鹿一兰便也享受了这一优惠,与公爹连大肚子面对着面
跪在手推车的车面上,脖子上一根绳子将二人连在一起,成亲吻状脸对着脸跪在
独轮车上游街。
我们冀中那一带的手推车,其顶部很窄,也就一尺左右宽,二人双臂反绑着
跪在上面,要想求稳,是十分艰难的事,何况那手推车是独轮的,连胖子从小读
书,后来又在外地做官,驾驶独轮车的技术偏低,其父亲又因腿脚有伤难以自持。
连大肚子一家特别地吝啬,在旧社会对长工和穷人也十分地刻薄,人缘不好,鹿
一兰狗仗人势,在与林大可私通时更是得罪了不少人,于是二人游街时便受到群
众的强烈的打击,一些不坏好意者动不动踹上一脚,于是就可想而知,游街只进
行了不到一百米,连大肚子和鹿一兰便被摔下来好几次。
鹿一兰从小练功,按说掌握这点平衡应该没问题,怎奈双臂反绑,脖子上又
有绳子与其公爹拴连在一起,便每每也和连大肚子一起,象两块死肉一样重重地
跌到地面,发出哎哟哎哟的惨叫。
革命群众的耐心是足够的,每每二人摔到地面,都会极热心地将二人重新架
起来,弄到独轮车上,由连少华继续推行着游街。这还不算,群众还要求二人亲
嘴,二人不敢不从,于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公公,一个三十多岁的儿媳妇,嘴对
着嘴、舌头缠着舌头地亲起嘴来。
「快看呀,公公和儿媳妇亲嘴。」
「哎!光亲嘴有什么意思,不如让这老地主给他儿媳妇亲脚丫吧。同志们,
你们说好不好?」
哪有不好的,一呼百应,全都说好。于是,二人由原来的跪在独轮车上,改
为骑坐,鹿一兰的鞋袜被扒去,一只娇嫩的脚丫被举到公公的脸上。
「狗地主,把你的狗嘴凑上去,快点,你妈的。」
那老地主,在无数双革命的大手的摆弄下,乖乖地将脸凑到儿媳妇的脚底处
……
「不能光亲,让他们喊起来。」
「对对,臭破鞋,你先喊。快点。」
于是鹿一兰开始喊了,「我这破鞋……没有底!」
这都是程式化的,早就被人教了无数遍,连大肚子便紧接着喊道:「我最爱
闻……这个味!」
人们对对着仍然艰难地驾着独轮车的连少华,「喂!四眼,你也得喊两声呀!」
连少华不敢不喊,于是他一边继续推车前行,一边按照要求喊起来:「我媳
妇和我爸爸搞破鞋,打倒狗地主连大肚子!打倒臭破鞋鹿一兰!」
……
鹿一兰被基本批倒,前几天还狐假虎威趾高气扬的这个南方女戏子,转眼间
变成了过街的老鼠。一天的下午,我和妈妈都收工回家,妈妈做饭,让我去院墙
外抱柴禾,刚刚走到低矮的土墙门口,就看见鹿一兰挑着两个大粪筒极不熟练地
歪歪邪邪地走过来,我象是欣赏一件什么稀奇的东西,愣在那看着那婀娜的身段
蹒跚地向着我家的方向走来。这时,我的身后,与鹿一兰相向的方向,有躁杂的
说话声音,我回头看,男男女女大概有十来个,手里挥舞着红色的小旗子,象是
要开什么会议似的,一边说笑着,一边也从另一个方向朝着我家的方向走来。这
些人都是郭二麻子属下的「从头越」造反组织中的革命闯将。我下意识地再回过
头来看鹿一兰,她无疑也看到了这群红卫兵,慌张地紧走了几步,到了赵小凤的
家门口,便象个贼一样地急速地闪了进去。赵小凤家与我家的隔离墙只有一米多
高,根本挡不住视线,只见鹿一兰进到赵家门里,正欲蹲下以躲避那帮子红卫兵,
却被赵大婶碰到,只听她大声地斥问:「你进来干什么,我家厕所又不在院里。」
「四姐,让我躲一躲,他们过来了。」鹿一兰压低了嗓音,蹲在地上,一边
不断地偷看街上那一帮子人的动向,一边求饶地说着。
「躲什么躲,给我滚出去,你个破鞋。」赵四婶一点不给情面。
「四姐姐,别这样……他们碰到我会斗我的……」
不等她说完,赵四婶大声斥道:「滚!再不滚等他们过来了我让他们把你揪
出去,滚滚!」
鹿一兰几乎是被赵四婶推着又挑着粪筒走出了赵家门,这时,迎面而来的那
帮子红卫兵已经距离很近了,她慌不择路的急急走进了我家的小院。
「小北,让我躲一会。」她害怕地对着抱了柴禾也进了院子的我说。
因为久等我抱柴禾而没进屋,妈妈恰好在此时也走到院子里,正碰上鹿一兰
进来,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鹿一兰几乎是颤抖着双腿对着妈妈说:「郑老师,
我在您家躲一会,碰到他们又要斗我。」一边说着,一边不等妈妈同意,却又急
速地找寻能够藏身的地方,可我家的小院净光光的,并没有能够藏一个人的地方。
妈妈冷冷地看着她,大概想说什么,也许根本就什么也不想说,只是直直地
看着她,象是看一个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这时,那帮子人已经走近了我家,妈
妈从矮墙上已经看到这帮子人,便象避瘟神一般地急忙转向,想往屋子里走……
「我到您家屋子里躲一会行吗?」鹿一兰一边说着,一边却全不顾我妈是否
同意,便也追着妈妈向着我家的屋子走去……
就在这时,那帮子红卫兵拥进了我家的院子。
「鹿一兰,你这破鞋,你躲什么躲,又干什么坏事了吧。」
「两个破鞋在一块,一定是策划反革命政变。」
红卫兵们的这两句话,就象是施了定身法术,鹿一兰和妈妈二人都停住了了
脚步,两手紧紧地贴着大腿两侧,低下头去,双腿并拢到一起保持了立正的姿势,
连呼吸似乎也停住了。
「什么他妈的政变呀,怕是策划怎么让林大可一个操两个吧。」
鹿一兰吓的动也不敢动一下,站在原地,全身甚至开始了抖动。
「鹿一兰!」一个女红卫兵大声喝道。
「有。」鹿一兰将头夸张地低下去,赶忙回答。
「你心里有什么鬼,见了我们东躲西藏的,老实交待。」
「对,老实交待。」
红卫兵们七嘴八舌地质问,鹿一兰双腿打着颤,半天才嚅嚅地回答:「没…
…我……没,我……怕挨斗。」
「把粪筒挑一边去,真他妈的臭。」
鹿一兰乖乖地将大粪筒挑到了墙角,又重新回到院子中央,低头站好。
「这破鞋肯定偷了什么东西了,你看这鼓鼓的」,一个个头不高但特别壮的
小伙子,用手指着鹿一兰的胸部,说,「里面肯定藏了什么东西,说,藏了什么?」
另一个坏小子赶忙接过话茬,「对,前几天生产队丢了茄子,说不定就是她
偷的。」一边说着,一边将手摸到了鹿一兰圆鼓鼓的大奶子上。
鹿一兰抬起手来,本能地想去推开那支罪恶的手,但只是举了起来,却并不
敢真的触碰那手。
那坏小子却并不放开,仍旧问她:「这是什么,老实交待!」
鹿一兰被问的害怕,却只是苦苦地看着那人,摇着头,嘴巴一张一合的,却
没有一个字出来。
「说呀!妈的这是什么?」
不能再闭口,便羞辱地:「是……嗯……嗯嗯……奶子……」
「他妈的不老实,奶子有这么大的吗,肯定是茄子。」
「对,肯定是,臭破鞋,把衣服解开。」
「快点!你妈逼的想抗拒改造是不是。」一个小子说着,扬手就是一耳光。
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你一个耳光我一脚的摧逼下,鹿一兰无奈地将上衣的衣
扣解开……
「他妈的逼的,你们看,这骚货里边还穿着一个奶罩呢,妈的,把奶罩撩起
来。」
鹿一兰双手抓住能罩的下沿,快速地将其撩起来,又快速地复原到原位,扬
起可怜的小脸,看着那个叫的最凶的家伙,象是在说,「你们看吧,是奶子不是
茄子吧。」
「妈的你晃我们眼呐,看都看不清楚就盖上,重新撩开!」
鹿一兰又一次撩开胸罩,又一次快速地盖住。
「他妈的!」那个又粗双壮的家伙一个耳光打在她的脸上,「撩着,让你放
下去再放下去。」
鹿一兰又一次含羞地撩开了胸罩,露出圆滚滚的一对大奶子,这一次,她的
手仍然试图向下盖住,但动了几下,都没敢真的盖住。
「转一圈,让大家看看,是茄子还是奶子,给你一个清白。」
无奈而又无助的她,就这么撩着胸罩,露着双乳,原地转了一圈,然后没等
同意,便快速地将胸罩重新罩住自己最羞于见人的地方。
「鹿一兰,听口令,原地跑步——走!」
鹿一兰象个军人般原地跑步了。
「一二—,一二一,他妈的腿抬高点,哈哈!」
我站在圈子外面,看着一群红卫兵象耍猴一样的耍弄着这位昔日红透山城重
庆的女戏子,心中荡漾起一种慕名的兴奋。
「鹿一兰是林大可的走狗,让她爬一圈。」
「不行,要爬三圈。」
「对,三圈,要一边爬一边学狗叫,快点!」
在红卫兵们的逼令下,鹿一兰双膝着地,双手着地,在我家的院子里爬行,
一边爬,一边口中「汪汪」地学着狗叫。引得众红卫兵们一阵阵地大笑,有的人
便不断地用脚踢她的屁股,有一个小个子的红卫兵甚至骑到她的后背上,「得驾
得驾」地象是骑马一般。
在这期间,妈妈一直侧立在一边,她想走,又怕一动会被人注意到她的存在,
于是小步地挪动着,挪到那一圈人的外侧,使劲地低下头,以此来减少被人注意
的机会。
果然,也许真是妈妈这样的作法凑了效,也许是妈妈早已被打倒批臭,没有
刚刚被打倒的鹿一兰那么令人有批斗的欲望,也许是魏副政委的特别照顾,在红
卫兵们玩弄鹿一兰的时候,几乎没人去弄她。
但几乎并不等于全部,其中就有一个高个子男红卫兵,走近妈妈身边,问道
:「鹿一兰到你家来,是想策划什么反革命行动,嗯?你这破鞋。」
妈妈使劲地将原本就低垂着的头再进一步地向下低下去,小声地回答:「没,
我不敢。」声音小的象蚊子。
那个红卫兵伸手去捏妈妈的脸蛋,摸了一会,又将手指伸进妈妈的口中,胡
乱地搅着,妈妈的头随着他手指的搅动上下左右地动着,还自觉地将双臂背到后
面,只是偶尔偷看着那人,脸上写着恐惧与哀求,却一丝声音也不敢出。待那人
的手刚刚松开她,便赶忙继续将头低下去,低到比刚才更低。
也许那红卫兵的兴趣仍然在鹿一兰身上,没说什么,便又回到鹿一兰周围。
折腾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样子,人们玩够了,要走了,又有人出主意,要鹿
一兰顶大粪筒,于是,鹿一兰被命令跪在子中央,一个装了半筒屎尿的大粪筒被
举到了鹿一兰的头上,命令她双手向上扶稳了罚跪,并交待给妈妈:「郑小婉,
你给我看着她,太阳没落山,不许她动一下,敢偷懒的话马上报告,不报告的话
连你也一样处置。」
妈妈低头应道:「是。」声音仍然极小。
红卫兵们玩够了,才又说笑着离开了我家小院。
看他们走远了,妈妈对我说道:「去抱柴禾,该做饭了。」说完连看一眼鹿
一兰也不看,自己先走进了屋子。
我抱了柴禾进了屋子,院子里便只剩下头顶大粪筒罚跪的鹿一兰。
尽管只有半筒粪便,但长时间老这么举着顶着,没过多一会,哭声便从鹿一
兰的喉咙里传出来。太阳似乎比往日下的都慢了许多,尽管收工已经很久了,却
仍然高高地挂在西天上,映出火红的晚霞。
妈妈做饭时,我先是在屋子里向外看,看鹿一兰罚跪的样子,然后又耐不住
好奇,又借故跑到院子里,近距离地欣赏这幅美女顶粪图。
「小北,我举不动了,呜……」鹿一兰哭了起来。的确,别说装了半桶的粪
便,就是一支空筒,双手老是这么长时间地举着,也够累的呀。
我站在那里,发起呆来,说心里话,我也有点怜悯她,尽管她对妈妈曾经那
样的虐待,但此时此刻的她,又显得那样的无助与弱小。
「小北,进屋子来。」妈妈站在中间的屋子门口喊我。
我转身欲离去时,鹿一兰又一次哭着对我说:「小北,让我放下来一会,休
息一会再举行吗?」
我小声地回道:「行不行又不是我能说了算的。」但我心里是明白,她这是
想偷懒而又想求妈妈别报告给红卫兵。
我进到屋子里,妈妈问我她说了什么,我告诉了她,她什么也没说,便让我
吃饭。
饭吃过了,妈妈开始收拾碗筷,院子里传来赵四婶的声音:「臭死了,滚,
滚出去!」原来是赵四婶隔着矮墙对着鹿一兰说话。鹿一兰又是无奈又是害怕地
回答:「四姐姐,他们规定我必须顶到太阳落山的。」
赵四婶回答:「我让你走你就走,你想把我们都熏死吗?滚远点!」
鹿一兰还在说什么,声音太小,没听见了。可过了没多一会,她静悄悄地来
到了屋子外面,没有迈步进入屋内,就站在门口看着妈妈,说道:「郑老师,是
赵四姐让我走的。」
妈妈看也不看她地回答:「那你跟我说什么?」
鹿一兰又停顿了一下,半天,才又说:「太阳……还没下山。」
妈妈不再理她,将洗过的碗放进碗柜,将一盆涮碗后的脏水朝着屋外泼去,
脏水泼到地面上,溅起的水滴和泥点好多飞到了躲闪不及的鹿一兰的身上。鹿一
兰大概还想说什么,但妈妈已经用力地将屋门关上,进了里屋。
我从窗户上朝外望去,看到赵四婶仍然隔着矮墙对她说着什么,她无奈地将
两个粪筒挑起来,走出了我家的院子,但今天的太阳仍然象是被什么东西给支撑
住了似地还迟迟地不下山,她抬头看了看,想走又不敢走地停止在了我家用几根
木头架着的全无任何实际意义的柴门处,象个作贼的似的,东边瞧瞧,西边望望,
好半天才重新迈步向外走去。
若本站收录的文章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删除侵权内容!
警告:本站立足于美利坚合众国並遵守美利坚法律服务于海外华人,谢绝中国大陆地区访问!
如您未满十八岁或当地法律不允许之年龄、亦或者您对本站内容反感,请自觉离开本站!
寻艳回首 :https://xunyanhs.github.io
聯絡: [email protected]
如您未满十八岁或当地法律不允许之年龄、亦或者您对本站内容反感,请自觉离开本站!
寻艳回首 :https://xunyanhs.github.io
聯絡: [email protected]